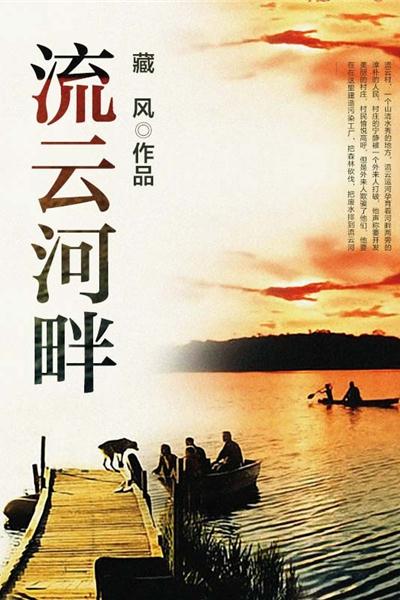每年夏秋之际,昆仑山积雪融化,山洪裹挟着石头泥沙从人迹罕至的大山中突围而出。千里河床、千百年岁月,滚滚激流把石头最强烈的个性磨砺得温顺润泽,使它们成为石头中的王。
“科长,您一年去几趟和田?”坐在火车上没事干,岳明要用科长丰富的阅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看那边出玉的情况,一般都要两三趟。”科长轻松回答。
“两三趟?扬州到和田有多远?”
“也就八九千里的路吧。”
“八九千里?那是多远?”
“走一趟你就知道了。” 科长喜欢岳明的好奇多问,但这小子不识趣,在人瞌睡打盹的时候,问个死烦。科长吸烟控制着自己,以免情绪失控一头撞向车厢。
“科长,我们到了乌鲁木齐,再坐火车到和田吗?”
“……我说岳明,你能不能睡一会儿?”
“科长,到了和田就能到玉矿吗?”
“去了你就知道了。”科长闭上了眼睛。
岳明把头伸向车窗外。他想起在家里的时候,岳川说去和田的距离相当于从扬州走起,逆流而上,把长江走尽。那得走多长时间呢?岳川又坏笑着说,如果是步行,恐怕你要走一年。
火车不停地进山洞,岳明看不到外面的景,也就睡着了。他希望一觉醒来就到乌鲁木齐,可是一觉醒来,车窗外更加得光秃秃,沙滩连绵。科长说,那是戈壁滩。
“这戈壁滩什么时候才能走完啊?”枯燥让岳明快发狂了。科长眼睛都不睁,他好像要把所有的觉都在火车上睡掉。
八十年代的扬州大大小小有上百个国营玉器厂,采购玉料都需要去玉石产地,采购人员是最辛苦的了,但真正能到达和田的,还是少数。岳明所在的玉器厂的实力在湾头镇是数一数二的,以加工新疆和田玉为主。科长是个能干的人,为不错过和田每一次的玉石分配会,他常年奔波在西去的长途路上。
为了这一趟充满诱惑而又未知凶吉的新疆之行,在极短的时间里,岳明花了不少心思打点行装,带了手电、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咸菜干粮。母亲说,北方山里冷,又给他带了棉衣。岳明是第一次出远门,他连续几天夜不能寐,兴奋、恐慌、期待都有。
出发的那天下起了小雨,他们穿着雨衣往南京赶,要到南京乘去乌鲁木齐的火车。科长说,不坐卧铺,可以拿到两块钱的补助。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六块两毛钱,出差还可以拿补贴,岳明开心地将母亲给带的鸡蛋全部放在了科长面前,科长也没客气,瞬间风卷残云。
俩人坐着硬座,艰难地挺了四天五夜到达乌鲁木齐。岳明下车立即欢蹦乱跳起来,年轻人有活力;而科长的脸却熬成了酱瓜绿,腰也哈了,腿也罗了。难道他每次出征,都把自己变成这模样?岳明投向他同情的目光。
在乌鲁木齐休整了一天,岳明只在旅馆周围走了一圈,还没看清新疆首府是什么模样,就被科长带上一辆军用的敞篷大卡车。
从乌鲁木齐到和田要走多长时间?岳明又问,科长就还是那句话:“走一趟你就知道了。”从科长淡定的样子看,一天?最多两天应该就能到。
大卡车上面摆着木头长条凳,乘客每人手上拿着一根大木棒子。这木棒儿要做什么用?
科长所答非所问:“最好用不上它。”
是要打狼吗?岳明一想到还要和野狼博斗,不禁寒噤。
出了乌鲁木齐,车便蜿蜒在戈壁滩上了,再后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除了天上的云在变幻图案,单调把人再一次逼疯。岳明没觉得枯燥,他无意中望了一眼科长,忍不住“哧”地笑了。才半天时间,科长全身就被尘土包裹,像一尊兵马俑,只剩下两只眼睛在动。
科长瞪着岳明:“臭小子,你和我一样。”
岳明再看每一个人的样子,便明白自己的土模样了。但他仍然坚信,科长的样子一定最滑稽。
第二天的路程又是另一番情景,沙尘暴来袭,大地灰暗,不见天日,恐惧绝望令一车人窒息。岳明缩在车角感觉自己被卷入了混沌,这下别说是笑科长,连科长在哪里都看不到。一定要活着到达和田,是岳明的唯一信念。
轰隆一声,车陷进了沙漠。全体人员跳下车嘿呀哈呀地拿木棒子往上抬车。原来木棒子并不是为了打狼,而是为抬起陷进沙漠的车而准备的。刚抬上来的车,转眼就又陷下去了。这一天,车陷下去十次之多,他们拿着木棒子跳上跳下二十多次,直到筋疲力尽。
原来沙漠上本没有路,走的车多了还是没有路。
晚上到达南疆的某个小镇,住进政府的招待所。哎哟,一进房间岳明就被呛了出来,怎么全是干茅厕的味道?再进房间是被科长扯着他的耳朵强行带入的。实在臭得窒息,岳明不停地干呕。
“这是什么毛病?”科长很生气。
岳明捏着鼻子说:“我在家倒马桶都会吐。”说完就干呕个不停。
科长想了想说:“把脸伸过来。”
岳明警惕地看着他。
科长不由分说把他拉过去,将牙膏像一堵墙一样地挤到岳明的鼻台上,以阻挡臭味的侵袭。这办法果然有奇效,后来屡试不爽。几十年过去了,岳明很难忘记那个招待所的味道,也不喜欢牙膏的味道了。
好吧,解决了嗅觉干扰,可以睡觉了。一个大房间里一张大通铺,可以睡十几个人。
科长让岳明睡自己身边,他自己先脱了个精光,然后命令岳明:“脱!”
岳明脱下了外衣。
科长说:“再脱。”
岳明又脱了背心。
科长说:“还要脱。”
岳明看看自己身上仅剩的裤头,疑惑地望着科长。
“快脱啊!要一丝不挂。”科长不耐烦了。
有人发出猥亵的笑声。
“不是,科长,你想演哪一出啊?”岳明窘得快哭了。
科长说:“我想演空城计。”
岳明再一看别人,个个全裸着把脱下来的衣服高高挂起。这是搞什么鬼?
在科长的坚持下,岳明终于全裸着钻进了被窝。
“不这样,你小子明天没得衣服穿。”科长说。
“有贼吗?”岳明不解。
“贼不可怕,怕的是沙漠吸血鬼。”有人说。
岳明一脸恐惧。
“别紧张,就是虱子。”那人解释说,这里虱子奇多。你要是穿着衣服睡,虱子会钻进你的衣服疯狂侵扰你,直到你拼死抵抗抓狂急眼,主动把衣服脱光,脱下来的衣服已经被虱子集团军占领了,你不能再上身了。
岳明对裸睡很不适应,先是睡不着,睡着了也睡不踏实,感觉四面透风,半夜还会被虱子骚扰醒,抓痒恨不得抓到科长身上去。后来,时间久了,岳明不裸睡竟然睡不着了,这种习惯一直伴随他多年。
天亮了继续赶路,路途中的艰辛难以细述。吃饭也成了岳明心中的痛,面条吃到嘴里全是沙子。面馆锅台、饭桌上苍蝇像轰炸机,黑压压飞来,赶都赶不走。厨师熟练地将苍蝇拍打在面团上,然后若无其事地拨拉掉,面就下了锅。不吃怎么办?肚子不答应啊。
科长带的压缩饼干割裂了岳明的嗓子,实在难以下咽。科长生气地说,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哪有这些好东西吃,有草根和皮带就不错了。
一千多公里的沙漠,他们每天走十多个小时,走了七天才到达和田。邗江边长大,从未吃过苦的岳明,第一次知道了漫长、孤寂、艰苦这些词的含义。科长总说的“去了你就知道了”,只有岳明能感到这句话背后的阴险。
从扬州一路向西北,马不停蹄十三天,加休息一天,近半个月。“以前的人到和田都是靠骆驼和马,走走停停要两年呐。现在有车,我们不到半个月就到了,那是多大的进步啊。”一路上科长都在忆苦思甜,否则岳明真要半途而废了。那些年,学校、工厂,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开忆苦思甜大会,岳明终于明白了它的意义。
总算身在和田了。总算亲眼看到了盛产籽玉的母亲河。
从莽莽昆仑的崇山峻岭中,蜿蜒曲折流淌出两条河,一条叫喀拉喀什河,一条叫玉龙喀什河。两条河在塔里木盆地交汇,形成和田河。喀拉喀什河出产墨玉,人称墨玉河;玉龙喀什河出产白玉,就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的白玉河。白玉河的籽玉从何而来?是河里自产的,还是山上的原生矿经剥蚀后被山洪冲到河流中的?它经常分布在河床附近,或者裸露,或者被掩埋在地下。虽然现在已看不到祼女月夜下河采玉的美景盛况,但目睹从昆仑山山谷滚滚而来的河水,岳明内心仍然激情澎湃。
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玉有山产、水产两种,各地之玉多产在山上,于阗之玉则在河边。”李时珍不知,于阗山上也产玉,只是后来才发现。
每年夏秋之际,昆仑山积雪融化,山洪裹挟着石头泥沙从人迹罕至的大山中突围而出。千里河床、千百年岁月,滚滚激流把石头最强烈的个性磨砺得温顺润泽,使它们成为石头中的王。
看到白玉河,岳明身心俱疲的“亏损”也得到了巨大的补偿。
在人类历史中,河流总是承载着比海洋更深厚的人的命运。千百年来,和田人取玉,主要靠从河里捡捞。洪水来了就意味着财富来了。上天安排了如此美事给这些沙漠中人,是不是对他们长期面对黄沙的一种补偿?自古道,在山吃山,靠水吃水。关键还要看谁有运气遇到美玉。
和田玉有山料和籽料之分,以籽玉的质量为上乘。羊脂白玉就是上品中的上品,极其名贵。现在,河床上的每一块石头都光溜溜的,充满了油脂,显然被千万人摸过千万遍。但它仍然变不成羊脂玉。
“你知道吧,”科长说,“咱们厂是做大摆件的,更需要大块的山料。要想得到好的山料,就要到于田县的阿拉玛斯玉矿去。”
“上玉矿?”岳明高兴地直跳。
科长郑重地说,省点力气吧,到达和田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艰难的路还在后面呢。岳明想起岳川经常念诵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便脱口说,“再难也没有蜀道难吧?”科长说,“唔,不说难于上青天,也差不多用手能摸着天了。”
这个时候的岳明已不是心里暗暗叫苦了,而是由衷地敬仰起常年跑和田的熊科长,原来英雄就在自己身边。一定要跟着这样的共产党员出生入死。想到之前,自己在工房过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舒服日子,内心有点小惭愧。
从和田市到于田县乘汽车四个小时。从于田县再到阿拉玛斯矿,要车行一百多公里先到流水村,也叫石头村。从流水村再步行羊肠小道九小时,到达矿区。这一路上,岳明一直在给自己鼓劲——爬山的时候不能落在科长后面。
科长似乎看出了岳明的紧张,开始给介绍当地的一些情况,想以此分散岳明的注意力,让他放轻松。
科长说于田是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它是古扜弥国所在地,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阿拉玛斯玉矿是新疆开采原生玉矿最早的矿区之一,是1957年在民国开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生产白玉的主要玉矿。维吾尔人说,玉矿都长在眉毛上,他们把山比做人,认为玉脉就藏在眉毛的位置,也就是在高山之巅,海拔高达4500~5000米之处。
汽车停在了流水村。
接下来就是靠人工运输的羊肠小道了。那是真正的羊肠小道,一面是山,一面是万丈悬崖。岳明往悬崖下扔了一块石头,等了半天,竟连一点回声都没有。天哪!深不可测,要是自己一不小心掉下去,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在这里,没有恐高症也会吓出恐高症来。据说,很多矿石就是在这样吓破胆的小道上靠人工运送下来的。
岳明手脚发抖,跟着科长一路攀登。
慢慢地,腿不听使唤了。科长问他:“岳明啊,是不是嘴唇发凉,太阳穴狂跳?”
岳明犹豫了一下点头承认。
科长又问:“还头痛耳鸣?”
岳明喘着气说:“科长,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也头痛耳鸣。这是都会有的高山反应,休息一下吧。”科长说。
坐了一会,所有的反应更加严重了。
岳明终于呼吸困难起来。
科长问:“要不要下山?”
“不要!”
科长破例向岳明竖起了大拇指。
“真犟!我没看错人。”
古人说:“去往昆仑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返。”那两人往呢?看看狂喘的科长,感觉很忧心。岳明不服气地望望荒凉的大山,把劲全用在了小腿肚上。
忽见一条山涧小溪清亮亮地流淌在眼前。岳明扑上前疯狂饮水。科长则挥臂朝着小溪上方扔去一个干透了的馕,然后不再理会地洗脸,洗手。岳明问为什么把馕扔掉了,科长说太干,咬不动。
“你咬不动,我咬啊。”岳明正要去捡回来,却见那块馕已顺着水流漂到了他们面前。科长把那块馕捞起来,掰一半儿给岳明。岳明发现,就这一会儿工夫,干馕已泡软了。原来馕是这么个吃法啊,真智慧!
在岳明眼里,科长此刻吃馕的样子又黑又酷。
前面还有多远?
没多远了。
怎么还不到啊?
翻过这个山就到了。
从日出走到日落,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科长的话总是让岳明的期望落空。岳明似乎再也打不起精神了,不是腿在走,而是身体在拖着两条腿往前挪……他感觉这一定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路。科长说,走完这条路,就没有你走不了的路了。
科长的话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度。岳明想起母亲“话到嘴边留三分”的提醒,否则真会恶语相向,炮击满口谎话的科长。
这回真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只有走下去才有活路。岳明暗暗给给自己打气——如果没有玉矿在前方,我怎么能翻得过山?如果不相信科长,又怎么能有力量……就在岳明眼前发黑的时候,阿拉玛斯玉矿像阿里巴巴的藏金洞神奇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岳明终于站在了昆仑山海拔五千米的高端,四顾茫茫大山,寒气逼人。那些险峻挺拔的山峰,冰雪,褐色荒坡,包括远处独飞的隼鹰,仿佛都给了他一种坚硬的力量。昆仑山让他变成了真正的男人,不管能不能得到良玉,这一趟都不虚此行。在这一刻,他觉得一路的奔波劳苦都不算什么。
望着嘴唇干裂的科长,岳明心底涌出深深的感激和歉意。科长啊,原谅我对你有过恶毒的诅咒,你一定要相信,那些诅咒都不会灵验的,因为我听说诅咒一个人自己也会受到损耗,所以,我的诅咒都不是真的。
岳川在岳明临走那天晚上为他补过课。岳川说,远古之时,天柱倾塌,九州崩裂,大火燃烧,洪水恣肆不息,以致民不聊生。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挽救了众生,又将所剩之石撒落在大地,“千样玛瑙万种玉”由此而来。这个神话将玉说成补天之物,可见玉是有神力的。
女祸洒满昆仑的千样玛瑙万种玉,也许只有在西王母时代可见。而如今,玉矿是露天开采,玉脉如游丝,难辨首尾。矿工们用錾子、榔头、铁钎等工具凿石取玉。因为开采方式效率太低,他们曾用过打眼放炮的办法,可是那样做有把好玉炸伤的危险。
有人把昆仑山上的玉石称作“鬼石”。之所以叫鬼石,是因它藏于深山,埋在石中,难为人识,神仙也虚实难度。但那扑朔迷离的玉气,会在阳光下升腾,吸引着无数寻梦者前赴后继。采玉人不但要付出十分艰辛的劳动,要有一双识玉的慧眼,还要有遇到玉的运气。
科长说与玉相连的岩石叫玉石根,看起来像玉却是石,最难区分。取得不好,玉石俱碎,前功尽弃。
在岳明看来,昆仑山采玉人比那些种玉的神仙还要艰难。黄金有价玉无价,只有亲眼看到那些浩大的工作场面、极端艰苦的工作环境,才知道得到一块玉何其艰难。师父说,玉是大地之精华,它是经过造山运动的地火高温溶炼,再经过万亿年的冷却结晶才形成的,不能再造重生。
他们到达的第三天,玉矿就神奇地出玉了。
玉遇见水才能显露真容。高山缺水,岳明看到矿工们纷纷解开裤带,郑重地把每滴尿都淋在石头上面,石头瞬间露出细白的玉色。轰地一声,人们沸腾了。那场面就像过年,气氛热烈兴奋。灶上把要吃半个月的羊肉都拿出来一锅煮了。这种时候自然少不了助兴的美酒,高山缺氧不宜多喝,但酒不醉人人自醉。
就听维吾尔族矿工们热烈地唱道:
爱你爱你我真爱你,
请个画家来画你,
把你画在吉它上,
我又抱吉它又抱你。
……
新疆几大怪:离婚容易结婚快,
冬天的帽子夏天戴,
靴子不穿背起来,
光吃馕不吃菜……
欢闹了一夜,岳明刚闭上眼睡着,就被科长拍醒了。“可以下山了。”科长说。
岳明惊喜地问道:“好玉到手了啦?”
“这个玉我们拿不到的,要去和田玉石分配会上拿。”科长似乎全忘了上山前说的话。岳明感到自己又上当了,“那我们像牲口一样爬上来做什么?”科长认真地说,“让你小子看看昆仑山、看看玉矿啊,这是你这辈子都求不来的福气。你别瞪眼,下次来再来和田,你就要感谢我了。”
“下一次?我还有下一次?”岳明差点喊出来,“科长,你在开国际玩笑!”
科长一脸正经:“我从不开玩笑。”
“那我问你,我玉雕学得好好的,你怎么就想到要调我来供销科?”这是岳明最想知道的事情。嘿嘿,科长狡黠地笑了,“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来和田参加玉石分配会的采购员来自全国各地,上海、北京、天津的都是大客户。岳明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科长抓紧落实他的传帮带职责,不厌其烦地给岳明介绍采购玉的门道和玉石行里的熟人。
“岳明啊,我们这一路所有吃的苦都是为了现在,就为能给厂里买到好玉。有了好玉才能出好产品,才能卖出好价钱,才能养活厂里的老小。”科长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感情,让岳明差点以为他是好人了。
岳明是学玉雕的,当然知道好玉是厂子的命根子。他向科长伸出手说:“科长,借我点钱。”
科长一怔:“你要钱做什么?”
“我看各矿的矿长都在,还有玉石收购站的站长,我想请他们喝个酒,请教请教。”岳明说。
科长扬手打了岳明一巴掌:“你小子,机灵!”
“哼!我哪有你机灵。”
矿长们并没有接受岳明的邀请,但新疆人敞亮,他们对这个热情敬业的扬州小伙子有了深刻的印象。
按照科长的嘱咐,岳明把收购站分配给他们的成堆的玉石做了登记,可是怎么运回去啊?“运输的事不用你发愁,”科长说,“现在交通工具方便了,汽车火车联运。以前你知道和田的玉石原料怎么运到皇宫里吗?我告诉你,那时候运原料可全靠牲畜和人力。大的原石,夏天用滚木,冬天用浇冰,去北京一个往返得两三年。”
听科长这么说,一个维吾尔大叔走过来:“我爷爷的爷爷说,那时候石头一出河就杀牛,用热着的牛皮把石头一包就拉走了。”
“为什么要用热牛皮?”岳明问。
大叔说:“热牛皮软嘛,越走牛皮越干,把石头包得越紧。这样好运输,还保护了玉石。”
岳明听得津津有味。
和田玉石分配站的站长尤茹祥接过话茬说,清末的时候,白玉河出了一块几吨重的优质籽料,地方官员命几十人用滚石的办法往皇宫送。走到半途听说皇帝倒了,皇宫的人也都跑了,这帮人把石头扔在戈壁滩便往回走。
“后来呢?”岳明问。
尤茹祥说:“后来听说那块石头不断被人分割,再加上日晒风化,变成山流水或沙子了。”山流水料是和田戈壁滩上的一个玉种,由于原生矿受自然剥蚀以及泥石流、洪水和冰川的冲蚀搬运而形成。
“真可惜!”岳明叹了口气。尤茹祥问可惜什么,岳明说:“可惜那块玉啊!世界上没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玉不能再生,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了。”
尤茹祥深深地看了岳明一眼。
这次因为科长和岳明的努力,和田玉整货车地拉回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为采购工作的新人,岳明在厂里小小地红了一把。
那天,岳明正指挥着工人卸货,不时用袖子擦拭脸上滚落的汗珠,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身着浅绿色连衣裙,像水中飘来的荷叶轻盈地来到岳明面前。她掏出一方手绢递给岳明,声音极甜极清地说:“师哥,接着。”岳明迟疑了一下接过手绢,不等他说话,女孩子已经跑走了。
工人们目光闪亮地追随着女孩儿的背影,转而又羡慕地开岳明的玩笑:“哎,苏婵的手绢什么味道?是不是甜香甜香的?”“她怎么就只给你送手绢?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岳明红了脸,他看看手绢,轻轻把它装进了衣兜。
工人们说的苏婵,就是岳明的师妹婵儿。在岳明眼里,师妹是一首诗,一朵花,不,是一块玉,他想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比喻都给她。岳明从和田回来去见了师父但没见到师妹,他专门给他们带了和田的大枣和核桃。师父说:“岳明,好好干,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句话把岳明想返回玉雕房的念头硬是给断了。
岳明算是有过见识的人了,回到家讲话也有了份量。尤其是昆仑山的故事,他给弟弟岳川就讲了三天三夜,当然很多话是重复的,重复就是力量。岳川现在望着哥哥的眼神是钦羡崇拜的,倒马桶的脚步是飞快的,态度是主动的。哥哥那套雕玉的工具,尤其是那把刀,在岳川的软缠硬磨之下,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岳川曾跟着父亲去厂里,在厂院里拣了块废料,回来就用刀比划,还请岳明指点。岳明发现岳川雕玉很有灵气,他对父亲说,岳川真该拜单常青为师。父亲却说,不去,岳川是上大学的料。
岳明也希望岳川能够考上大学,就因为高考的日子将近,岳明才没逼他续写“一捧雪”的小说。没想到岳川在晚上悄悄交给他一个作文本。
李莫明含恨而去后,第二天夜里,珍品斋遭劫,学徒单常青险些遇难,“一捧雪”赝品被盗。苏州城玉器行老板黄玉泉闻声而来,说若能一睹“一捧雪”风采,此生无憾。可是珍品斋的玉匠陆永冈拿什么给他看?黄玉泉为此茶饭不思,连日查看史书。根据《明史》和《张汉儒疏稿》的记载,“一捧雪”为明代著名玉杯,当时的权臣严嵩欲将玉杯据为己有,玉杯的主人莫怀古弃官改姓隐居他乡,“一捧雪”在嘉靖年间失踪。
李姓人氏不远千里专找陆永冈仿真“一捧雪”,那真品在哪里?
陆永冈虽然不是陆子冈的传人,但他的手艺也是专诸巷数一数二的,如果他真能仿制“一捧雪”,那真品出现就为时不晚了。于是黄玉泉选了一块上好的和田白玉,找到陆永冈,要他为自己仿制“一捧雪。”陆永冈正为赝品丢失烦忧,虽然李莫明身亡,但他的家人一定还会找来。他拒不接受黄的请求,说除非有真品在此,否则无法仿制。黄玉泉大为郁闷。
夜深人静时,陆永冈悄悄来到工房,开始仿制“一捧雪”了。他没有见过真品,就连赝品也只是一面之缘,但他想试试,因为他相信李莫明的家人会找来,从他手里丢掉的东西,他一定要还。在他身侧的门板鏠里,有一双眼睛,那是单常青在偷师学艺。
单常青明白,“子冈玉”的雕刻技艺至今仍属绝技,难以仿效。清代以来不乏赝品,其中也不乏高手所为,但雕刻水平毕竟与子冈玉相去甚远……
“笃笃笃!”不等里面答应,岳明就闯入了岳川的房间。他气呼呼地晃着作文本问岳川:“这是谁写的?”
“我呀。”岳川得意地说,“这么快就看完啦?有点意思吧?”
岳明把作文本摔给他:“告诉你,把单常青的名字改了,否则我跟你没完!我师父怎么会偷师学艺?你诬蔑他,就等于诬蔑你哥!”岳川拣起作文本:“你没看完就动怒,单常青是想偷看昆吾刀才……”
“偷看?那更不像话!”
“婵儿听了都说好,你又是为何?”
“我不管你那么多,改!马上改!”
“不改,你再也看不到小说了。”
岳明没理弟弟,走了出去。岳川在他身后喊:“哥,我还写了《昆仑神话》你要不要看?”
岳明头也不回:“昆仑神话是你也可以写的?”
很快和田那边打来电话,矿上又出了好玉。科长对岳明说:“去吧,我已经带你走完了全程,以后跑和田的专利就是你的了。”
岳明顿时想起科长曾经变态的笑脸。
为使岳明轻松,科长说:“玉矿你就不用去了,直接参加玉石分配会就行。”可岳明并没有感到轻松。
科长语重心长地说:“岳明啊,放你单飞,可是厂领导对你的信任啊。我让你一次尝尽苦头,就是为了让你具备免疫力,再去和田如蹚平地,这一点不骗你的。”
岳明大脑空白。
“怎么?你不愿意啊?”科长做出要揍人的架势。
岳明把头迎上去。
科长真的一拳打了过来,拳头到了岳明头上却变成了手掌抚摸,“岳明啊,你前途无量,科长不会看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