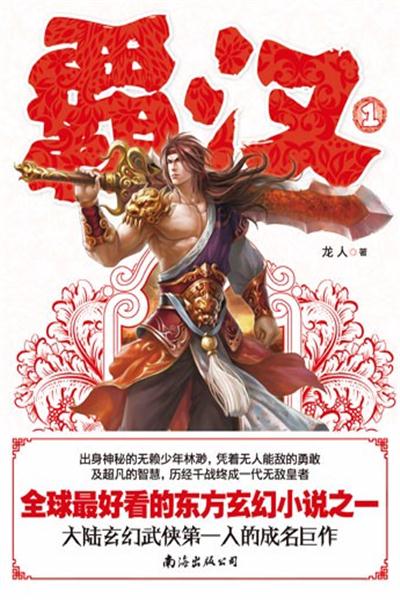朴石安看到的是一座荒庙,虽不算破旧,但已长久没有人来添香火了。几尊露出了泥坯的菩萨,有的断臂,有的缺耳少鼻,有的东倒西歪,形貌甚是滑稽。
朴石安将马匹牵进庙中系好,这座庙有三间厢房,地面上到处是枯草败叶,残砖碎瓦,这荒庙里最活跃的东西当数蜘蛛,它们不停地结网,这里大半空间均被蜘蛛网所占。
厢房很乱,而且也很潮湿,倒不如在庙殿里伴着这几尊荒神。凌真儿早已收拾好一片地面,坐的有现成的蒲团,再在庙前找些木板木棍燃起一堆篝火,倒也十分惬意——无论如何比做落汤鸡要舒服多了。
拿出干粮,二人边吃边旁着火堆烘干衣服。
朴石安拿着酒袋,不时的喝上一口,不仅解渴,而且还可以御寒。而凌真儿则只有啃着干粮,痴痴地望着他吃喝,脸上总浮着微笑。朴石安又喝了一口酒,看了她一眼,笑道:“来,真儿,喝一口,暖暖身子。”他将酒袋伸向凌真儿面前。顿时酒气冲鼻,凌真儿忙向后挪动半分,摇头道:“不,我不喝!”朴石安笑了笑,反而将蒲团向前移了移,酒袋仍托在凌真儿面前。凌真儿忙伸手不让酒袋再凑近自己。朴石安笑道:“没事的,保证不会醉倒我的真儿,就喝一口。”说完,他硬是将酒袋凑近凌真儿。
凌真儿也是一时被迷糊了心窍,她心想:“喝就喝,不就是一口酒吗?非要硬着人家喝!”双手接过酒袋,看了朴石安一眼,还发出一声“哼!”,然后她果真举起酒袋,就着嘴灌了一大口。
不就是一口酒吗?可到了嘴里她才知道并不是滋味,呛人的酒气,辣乎乎的酒味,使她怎么也吞不下去。但是,这么一大口酒缄在嘴里那更不是个办法,不会喝酒的人缄着酒也会觉得难受。好歹她总算吞进了一小口,可剩下的她却无能为力了。“哇”的一声全都喷了出来,并不住地咳嗽。顿时凌真儿只觉得脸颊发烧,嘴中及肚子里都辣乎乎的似火烧一般,扔掉手中的酒袋,然后双手拍压着下唇,似乎想把入肚的酒呕吐出来。
朴石安本是好心,喝了酒后全身血液循环便会加快,能暖和身体,方才淋了雨也不会受风寒所侵。可没想到凌真儿当真是滴酒不敢沾,他这酒又比较烈,辣得他眼泪都快掉了下来。他忙移过身去,扶着凌真儿,左手不住的抚拍着她的娇背,歉然又心疼地道:“都是我不好,不该让真儿喝酒,害你受了这么大的罪。”他不说倒好,一说凌真儿便“哇”的一声,半真半假地大哭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拍打着他。
“啪”,一声脆响使的凌真儿顿时惊住了,她不哭也不闹,惊慌失措地看着朴石安,两手不知所措的伸着。只见朴石安的俊脸上慢慢现出了一个鲜红的掌印。原来,在凌真儿两手乱挥乱打中不小心拍上了他的脸颊。
这下子又轮到凌真儿来安抚朴石安了,她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小心地说道:“安哥,我——没打痛你吧?”她还伸出纤纤玉手轻柔抚上朴石安脸上挨了打的地方,刚才用这只手打人,现在又用这只手来安抚别人。唉,真乃善变的女人。
朴石安突然灵台一亮,知道怎么做可以使凌真儿又高兴起来。于是,他故意生气地说道:“哼,我只不过让你喝了一口酒而已,而你却要的要我耳光。不行!我要还你一巴掌。”他还作势举起右手,凌真儿刚才真不是故意的,她心中也充满了悔意,男人总是很要面子的,被女人打了一巴掌还怎生受得了?见朴石安说要还她一巴掌,她便马上仰起俏脸等待着挨打。但朴石安却又道:“你把眼睛睁着我怎么打?”凌真儿忙将眼睛紧紧闭上。
打人耳光,谁都知道那是需要用手来完成的动作。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朴石安打凌真儿的耳光却不用手,那他用什么呢?嘴巴!朴石安重重地亲在凌真儿的通红脸颊上,吮吸了很久才“啪”的一声撤回他的大嘴,并得意地笑道:“好了。”凌真儿羞喜交集,娇声道:“你坏死了!”然后别过头不敢看她。
忽然,朴石安无限痛惜且充满惊骇的大叫一声:“哎呀,我的酒!”凌真儿回头一看,只见他提着酒袋——空的。望着湿漉漉的地面,表情既痛苦又惋惜。原来凌真儿方才扔下的酒袋是没有塞上塞子,掉在地上。那里面的酒便流了出来。朴石安本舍不得嘴多而节约下来的这么半袋酒,却一下子让那土地神白白喝光了,他怎能不难过?他望了一眼那几尊高高在上的神像,发现那尊在最旁边的土地神像的神情是笑嘻嘻的,好象是在说道:“好酒!好酒!”朴石安气得眦牙咧嘴,挥舞着拳头恨不得将那神像一拳击个粉碎。凌真儿却在一旁拍掌笑道:“活该!现在你没酒喝的了!”朴石安闻言放下拳头,猛一转身,对着凌真儿“恶狠狠”地说道:“没酒喝,那我就喝你,那滋味也……蛮醉人的,可以吗?”
凌真儿知道他所说的“喝”是怎么样的喝法,小脸不禁一红——她的脸本来就红通通的,因此朴石安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他看得出凌真儿虽然羞答答的故意不依地板了他一眼,更不敢答他。但神情却是千肯万肯,朴石安本是说着玩的,可现在他几乎忍不住就要上前紧搂住凌真儿,用嘴好好地品尝一下凌真儿的滋味,大快朵颐。
接着便见朴石安畅快地叹息起来,凌真儿怎敢对视他那喷火的眼神呢?吓得闭上了眼睛,她或许不知道在激动意识下发生的动作,暗含着一层任君采撷,让君品尝的意思。
眼看凌真儿就要惹火烧身了!
蓦然,朴石安从怀中掏出一张人皮面具带上,并沉声对凌真儿说道:“真儿,有人来了!”然后便凝神静气地坐着。此时雨已转小,凌真儿闻言一惊,忙收起心神,坐正整理好衣物,用期待朴石安的目光望着他,没有言语,她知道朴石安会在该说的时候向她说明一切,因此没必要开口去问。
朴石安突然眉毛一皱,沉声说道:“一共有十三匹马,但似乎还有人跑动,咦?他们现在都停了下来,离这庙只有百丈来远,好象是有两个人被骑马的人围杀。真儿,我出去看看!”凌真儿也一跃而起,叫道:“我也去!”朴石安没有反对。
两人从庙后出门,后面是一片山林,比较容易躲藏,他们的轻功都至臻化境,快似行云流。朴、凌二人藏形于一棵大树后,离那群人只有几丈之距。
果真是混战在一起!只见两个身着破碎道袍的老者被十三名黑衣杀手呈半月形围着,他们都经历过一场恶战,其中一人头上没有帽子,而且头发散乱,显然是在激战中被人一刀(或剑)削掉的。另外一人相对来说不算太狼狈,只是嘴角淌着血,眼睛里布满红红的血丝(在朴、凌二人看来他们就像是长着一双红眼睛),神情充满愤怒与宁死不屈的坚强,还有一抹难以掩饰的疲惫。朴石安一时还看不出那两人是何门派,只觉他们都是不恶人,而那些黑衣杀手则个个身上布满杀气,都蒙着脸,且蒙巾头顶处有一个金色的制钱标志,用的都是相同兵器——九环砍刀。朴石安心道:“这些人莫非是漠西的金钱盟之人?但金钱盟早在十年前便从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据说已经解散。难道他们又重出江湖了?”
思忖间,已有一名黑衣人狞笑道:“二位,还不将本门秘笈交出来?”朴石安发现这说话之人与其他人装扮有一点不同——他的那个制钱标志处绣着一根羽毛,朴石安猜想这人一定是这群黑衣杀手的头领。
只见那没戴帽子的道士向水地上吐了一口血痰,骂道:“呸!你这魔头,当年你身负重伤,我师兄见你可怜才让你入观疗伤,没想到竟恩将仇报。你道貌岸然,卧底抽薪,偷走我镇观的紫阳秘笈。现在,我师兄弟二人总算夺回秘笈。亏你还有脸说这是金钱盟的秘笈!”这道长的眼睛里快要冒出火来,显然是心中气怒至极。另外一个道人却一脸正气,表面上看似是不愠不火,却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浩然之气,手中长剑归鞘静立当场,不似他师弟那般冲动。
那黑衣蒙面人却丝毫不动怒,大笑道:“牛鼻子,等你逃出此地再说这些体面话吧,哈哈……”其余十二人都跟着大笑起来,笑声从旷野中传了开去,声音洪亮,显然每个人都是内功不弱,他们如此猖狂,仿佛是猎人正盯着垂死挣扎的猎物般。朴石安暗叹:“这群黑衣人好强的内功,不知这两位道长是哪一派的人,看来他们已身受重伤,怎是那些杀手之敌?”他暗中按住剑柄,准备随时出击,凌真儿知其心意,亦不知不觉中紧握一把银针。
那黑衣蒙面人颇为敬重地说道:“冲灵道长,在下以前多有对不住的地方,但只要道长肯将秘笈交出,然后自废武功,在下还可以不顾师尊他老人家责骂,放二位道长一条生路。”在他看来,这已是最大的忍让了。
戴帽子的道长就是冲灵道长,他悲凉地高宣一声:“无量寿佛!”然后上前两步打个稽首,朗声道:“施主一定要秘笈的话,必须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他的师弟却在身后吼道:“师兄,绝不可答应这个魔头,我们宁可一死谢罪列代祖师爷,也绝不屈膝投降!”不料冲灵道长猛一回头,一改先前温尔风雅的态度,厉声喝道:“师弟,休得多言!”他师弟不服,又道:“师兄,这魔……”
冲灵道长喝道:“冲云,你敢不听观主之令?”他师弟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眼睛一亮瞪了那黑衣蒙面人一眼,便没有再言语。
朴石安正好与冲灵道长两相对面,看到他在厉喝之后,嘴巴嚅动了几下,他师弟冲云道长便没有再言语了。
那衣蒙面人见事情有了转机,大喜道:“冲灵道长,你刚才说什么条件?”
冲灵道长低头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再缓缓地沉声说道:“贫道接掌西天观已有十八载,而我西天观自祖师爷天安道长创观以来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贫道不才,却不愿西天观在贫道手中葬送。下一辈弟子中又无甚出众人才,当真天灭我观?贫道身为观主,虽有紫阳秘笈在手,却无法领会其中精奥武功,才出现了今日之局面。唉,唯有一死以谢列代祖师。施主一心想得到紫阳秘笈,贫道自忖武功不及施主,合我师兄弟二人之力,或可勉强为之。但现在贫道二人已筋疲力尽,施主又有众多功夫不弱的属下,贫道二人断难生还。因此,贫道只有将秘笈交出,倒不是贫道贪生怕死,人生在世短暂一瞬间。只是西天观中尚有百余弟子,贫道不忍让西天观至此断传。因此请施主放过观中一干人等,否则,贫道就是血战到底也要护住紫阳秘笈,即使护不住贫道亦不会让它落在施主手中。”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打不赢,也可以毁掉紫阳秘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