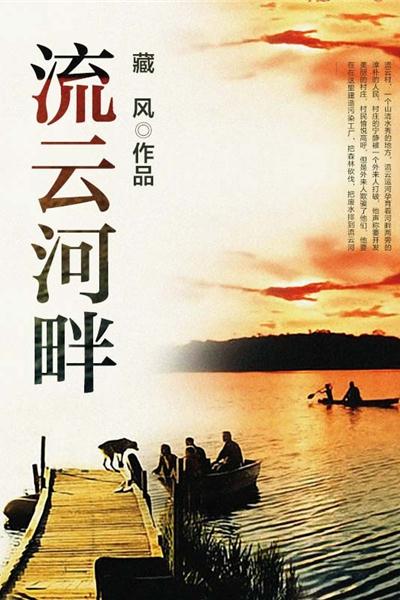开学一个月了,王小红终于回去了。李叶茴一早醒来看到地上一个空空的睡袋,感觉还有母亲的体温。王小红离开时的动作那么轻,而自己睡得那么死。
李叶茴舒了一口气,连窗外的天都变得格外蓝。她麻利地收拾好房间去上课。
一路上,伴着校车来来往往,高大的椰树和大叶桃花树迎风抖着鼓掌。随处散落的新鲜绿叶有着强壮的叶脉,像人类血管,一放一收地跳动,静静地盖着树桩上小憩的松鼠,也吓得蜷缩在树根的棕黄色变色龙快快变绿。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就像李叶茴肉眼可见的美好未来。
这一周的睡眠质量都是难得一见的好。李叶茴的饮食计划控制得也不错,虽然学校常常会举行各种活动也给学生提供数不胜数的蹭吃蹭喝的机会,但是之前忍饥挨饿的好底子让她没有过分反弹,加上运动,身材维护成绩斐然。
然而她发现自己难以融入课堂。A水准期间,李叶茴为了追赶进程,便脱离课堂、闭门造车,导致到了大学也听不进课,五分钟一走神,回过神来已然逻辑断链,只得回家自学。
还好学校会录制课程内容,供学生回家查漏补缺。
另一件不顺心是“寂寞”。
来新加坡快一年半了,李叶茴终于正眼看待孤独。王小红还在的时候一切正常。李叶茴白天上课,晚上和母亲在跑步。虽然王小红和自己并非百分百契合,但若没触及她的“爆点”,双方还勉强是对方的贴心伴侣。可是母亲一回国,这个和国内四人间宿舍一样大的单人宿舍就显得有些孤单了。
更何况这里没有班级制,学生还能自己设计课表,因此大家每天都上各自的课,下课回各自的回宿舍。如果没有特意社交,一个人完全可以将自己和外界完全隔开。所以,学校大肆鼓励学生参加社团也可能为了避免他们过度享受孤独。
李叶茴想留在Raffles Hall,就要参加Hall的社团。可因为这决定做得太晚,各社团早已关闭招生,不过这无所谓,因为她梦寐以求的Raffles乐队还在招新。
李叶茴重新捡起告别三年的小提琴、逼着自己用僵硬的手指重新按上琴弦。她只练一首还算熟悉的曲子《夏夜》,增大胜率。可面试时候她还是因为紧张坏了事。李叶茴的琴声吱吱扭扭,再加之大部分曲目在高音声部,无意中放大了每个音色的瑕疵。
面试当天晚上李叶茴就收到了拒信。
同时,张庭园被Raffles hall的乐队录取了。他不知道李叶茴悄悄跑去面试,还名落孙山,便约李叶茴一起跑步,顺便宣布这个好消息。
李叶茴嘴上夸对方才华横溢,心里却总是不舒服,跑步时把速度带得飞快。难以独手保持平衡的张庭园在后面跟得歪歪扭扭。
乐队不要她,李叶茴有些无所适从。剩下还招人的社团只有绿化社——每天除草、道具社——做木工活,乒乓球社、女足和羽毛球。这些和王小红所说的“女孩子应该高雅、端庄、有架子”相差甚远。一个做木工的女孩、踢足球的女孩、除草的女孩怎么才华横溢啊?怎么优雅大方啊?
李叶茴想着就没兴趣。可是想留下来又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她了解到Raffles Hall羽毛球社社长也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学姐,便用了一周时间和学姐搭上线,闲谈之余“顺便”表达了留Hall的愿望,和没合适社团做奉献的悲伤。
学姐身为同胞、马上透露自己的羽毛球社长身份,热情邀请李叶茴入队。
小计谋得逞后,李叶茴非常开心,还割肉买了昂贵的羽毛球装备。毕竟在她和王小红心中,羽毛球这个高高蹦起的运动,可是比“只能摔得一身泥”的足球要高雅得多。
Raffles hall是七个Halls里女生羽毛球队质量最高的,被称之为R-战队。
队长学姐的父母在中国均为省市级的羽毛球队教练。学姐从小耳濡目渲染,自然体育能力超常,小小年纪便因为羽毛球特长受邀来新加坡求学。她的才能不止于此,铅球、乒乓球、游泳……都是长项,被朋友称之为“能撑起一个运动会的女人”。
李叶茴暗想,如果自己能在羽毛球队崭露头角,也算是曲线救国,小提琴女神什么的不做就不做了吧。
可是一进羽毛球馆李叶茴就傻眼了:那些平时看起来瘦瘦弱弱的女生们一拿起拍子就成了战神,把比麻雀还轻的羽毛球砸得像是子弹一样极具杀伤力,令人眼花缭乱地四飞,“嗖嗖”声不绝于耳,就像冬日寒风般令人发颤。
李叶茴冷汗直冒,不自量力的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蠢事情?
终于,轮到她来“秀绝技”了:五个球全没接到。
对面还算涵养好的陪练队员没把不悦写在脸上,但她一边聊天,一边还能捞住李叶茴的歪球,轻轻一扫就让李叶茴狼狈地乱跑一通。
李叶茴耽搁了别人的进度,很羞愧,就老实去一边休息了。既献丑、又得罪人,而且一直捡球也提升不了球技,何必呢?
她老老实实坐在角落,看着那些热情洋溢的女孩子们窈窕的身体里迸发出无限力量。这女性力量赋予在小而灵活的羽球之上,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白线。
久违的自卑又来了。自己还能做什么呢?辩论队是顺利进去了,可是进了以后才发现,和能言善辩、学富五车的前辈相比,自己像个文盲。一直引以为豪的“感情切割”能力彻底消失,她的上场发言充满紧张,声音抖得像要掉渣,暴露出内心深处的无能。
除了动嘴皮子,她没有什么值得被认可的技能了。
跳舞?羽毛球?乒乓球?
要不真的去绿化社除草?或者道具社锯木头?自己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大学生活,实在是不甘心投入到这些不需智慧才貌的工作中去。
自那之后,每次羽毛球队训练休息时,她便一个人坐在角落背德语单词,看起来十分突兀。大家笑着闹着、讨论着赛场风云、分享着挥拍技巧,而力量不够、技巧全无的她即使虚心请教也只能让她更受排斥。在实打实的才能面前,浅薄的“和蔼可亲”根本就不能吸引朋友。
李叶茴发现自己苦苦建立的“自信”是肥皂泡,看起来流光溢彩、但随时可以灰飞烟灭。
最后,她还是放弃了羽毛球队训练,又没胆量和学姐明说。缺席几次后,学姐的慰问也让她尴尬,最后又成了多了一个见面要绕道走的朋友。
“多交朋友”、“提高社交能力”…… 这都是她的“大学必做表”的核心项目。可是自己的计划都或多或少有了残缺,就像裂口的堤坝,先是水流喷射,后被逐渐变强的水力彻底掀翻。
最后,她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加入了道具社和绿化社。每次除草她都能看见大厅内排练的乐队。张庭园正摇头晃脑、看起来十分专业地享受演奏。这更令她难受。一开始和他对话的自信和魅力一扫而净,只剩下忍不住垂下的眼帘。
李叶茴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努力。那些生来就“扮演精英”的人们不是自己的同伴、而是遥不可及的风景,那些错过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
带着久违的自卑,她发现,原来进入梦想院校不过是起点。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自己的学习成绩进展还不错,当然这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刷题折磨下换来的。
李叶茴对学术生活充满期待,毕竟从小到大人们都说:学习才是人间正道。她想废寝忘食奋斗上四年,去考满分、赢比赛、成为专业领域的掌门人,成为霍金、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乔布斯……去改变世界。
所以她采取的还是A水准期间用的最蠢但是最踏实的方法:“死记硬背”。她的记忆力已经被训练得突飞猛进,再加之失眠的治愈,学业顺风顺水。
李叶茴的同学都是经过多层筛选、背负着家族精英梦的学生,和高唱南洋的懒散氛围完全不同。每个人都朝气十足、做着大量的计划、进行每日恨不得24小时的社交。李叶茴觉得有压力,也有动力。更何况她在几堂课的随堂小测试都拿了名列前茅的分数,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天之骄子的影子。
另一个让人欣慰的是她和“神秘伴侣”进展。
那天李叶茴看到张庭园气喘吁吁地在身后摇摆不定地追着飞跑的自己,终觉不忍,停下来等待。张庭园又冲她挥挥手,示意她不用等待。
李叶茴有些犹豫。
于是张庭园露出自己标志的八颗“又小粒又洁白”的牙齿,眼睛里流淌出温柔的光,再次挥手示意她不用等待。
李叶茴这才继续飞跑,一圈一圈地超着对方,而张庭园从没抱怨过,按部就班地静静跟随。
那天晚上的李叶茴每超过张庭园一圈,她的心脏都少了一个角。那些零零散散的心脏碎片像一只只企鹅一样在她身后摇摇摆摆地追随。
自那之后,每周张庭园都会和李叶茴一起跑步两次。李叶茴再也没停下来等他,但是她感觉等待是“陌生”,不等待才是默契。结束跑步后,两个人就会绕着操场一圈圈散步。张庭园给她表演各式各样的B-Box,李叶茴则笑得合不拢嘴。
一天,张庭园问她想不想听他演奏长笛。
“好啊!戴着假肢吗?”李叶茴惊奇地睁大眼睛。
“嗯,我戴上假肢给你表演。”
于是李叶茴去了张庭园的屋子。房间的装饰显出张庭园优雅讲究的品味:房间中央躺着棕色羊绒毯,一朵香薰烛光在书架上静静燃烧,整个房间香得像是野花山谷。他有着各类高端电子装备,桌子上的笔和本子码放整齐。
他背对着李叶茴戴上假肢,开始了自己的演奏。
那是一个周二,克拉码头的酒吧街推出了女士免费的“Lady Night”,张庭园的邻居们都去狂欢了,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沉浸在音乐世界中。
李叶茴坐在柔软的地毯上望着他一脸的忘我,仿若看到少年单纯的灵魂。她希望时间暂停,但又害怕深陷其中。如果说没有动情是嘴硬,这样一颗柔软的灵魂怎能不令人好好欣赏、好好喜欢着呢?
但是他们没有可能。有着对女婿严格限制的王小红不可能接受别人的残缺。
“李叶茴,我要求不高。不要亲戚太多,不然给你找麻烦;最好是外国人,但是必须是发达国家的……印度首富也不行;还有,四肢健全我就不多说了,不然你自己也不会接受。”
王小红没说过:“对你好、性格温柔、善良懂事。”好像自己从李铎身上吃的亏还不够。
几年后,李叶茴情场受挫,借着“朋友情场受挫”的名义请教王小红。母亲说:“父母不会在乎孩子幸不幸福的,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
回忆到此为止,李叶茴的表情多了一丝哀伤。
张庭园表演结束后,坐到李叶茴身边,讲起自己不为人知的另一个故事:“你知道吗?我是个名人。”
李叶茴一脸哭笑不得:“你还说你是个帅哥呢!”
“我不帅吗?不帅吗?”
“帅……说说吧,为什么是个名人?”
于是张庭园开始讲述:
十六岁那年,年纪轻轻的他发现了新加坡服务类网站的“蓝海”,找了一帮计算机系的本科生、模拟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创业,竟成了本地同类产品的佼佼者。那之后的张庭园成为了本地互联网界的大咖级人物,在社交网站上起到了一定呼风唤雨的作用,身后也簇拥着数十万粉丝。
“那你来上学了,公司怎么办?”
“我跟我的合伙人说让他们先做着,好好等我四五年。毕业以后我会再回去的。”
李叶茴嘴上崇敬得不行,但内心还是留了心眼:张庭园的生活看起来充满各种传奇,但是很多细节不经考验。比如当初拒绝了米国大学的Offer,却是为了等待长居米国的家人?既然已经成为创业大咖,又何必等待他人捐赠的假肢……关键是张庭园口中描述出来的那个人太完美,无法和眼前这个平凡无奇的微胖男孩连接到一起。
李叶茴想要去张庭园的社交网站看看,以长见识的语气其实在验真假。张庭园没有说谎,他的“粉丝”果真有二十万。李叶茴心中发自内心地产生崇拜之情,就像她常常对有才华的男孩动心那样。
气氛一下子不再自然,李叶茴大脑一片空白,绞尽脑汁也找不到话题。张庭园静静地望着她,眼睛里克制地流露着深情。然后他俯下身,亲着李叶茴。
“不要这样。”李叶茴拒绝了,却动弹不得。她心里开始发慌。
李叶茴脑海中闪现出几个镜头:张庭园矮矮胖胖的形象和残缺的肢体、王小红威胁地说:“……我要和你断绝母女关系”、最罪恶的是,她竟想起李铎和李斌一脸嫌弃、嘲笑的嘴脸……她不能接受。她不想被看不起。
“不要这样。”李叶茴重复,却被内心怯懦的小人钉在地上、不能动弹。她不敢停止他,因为她不愿失去他。
王小红说:“不要轻易逼得人离开你。”如果爷爷生气了,你就没房子住了;如果叔叔生气了,你就没机会去高档餐厅了;如果父亲生气了,你就没有户口了;如果母亲生气了,你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如果张庭园生气了,之后那些孤独的日子又有谁可以做自己倾诉的树桩呢?又有谁可以为自己介绍新的人脉呢?又有谁可以提供各种有效的本地信息呢?
李叶茴打定心思无法动弹。张庭园仿若听到李叶茴内心呼唤。他停了下来,看着她:“我送你回去。”
李叶茴房间门口,张庭园问:“你也不开心,对吗?”
李叶茴的心思还在刚才的情景里,被猛地一问有些回不过神来。
“你没有你显现的那么开心。”张庭园重复。
李叶茴默认了,回问他:“你也有很多不开心吧?”
对方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想找人聊聊吗?”
李叶茴一脸疑惑。
“我明天过来好吗?”
李叶茴不知如何拒绝,于是茫然地点点头,一缩身钻进房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急促地呼吸。
这一晚,李叶茴开学来第一次失眠。她辗转反侧到凌晨两点才深深睡去,第二天又被穿透力极强的阳光唤醒。
张庭园和李叶茴之间的关系是两人的秘密,外人看来他们不过是点头之交的距离。她讨厌不确定感、正如她讨厌浪费时间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对于张庭园,她没有计划,只有不舍,深深的不舍。
那晚,李叶茴没有去自习室。平时一直敞开的宿舍门今天也矜持地关上。李叶茴静静等待着,忍不住笑话自己傻气。九点半时,敲门声响了,张庭园拿着饮料和食物推门而入进来。
“是Raffles hall举办了活动,有免费的吃的,我就拿了一点过来。”张庭园随意打量着她刚刚打扫好的房间,规矩地把拖鞋拿进来,整齐地摆放好。
他自顾自地爬上床,断臂放在身侧,整臂放在腹部。他穿着运动背心,兴致勃勃地望着李叶茴安静的背影:“困了吗?”
李叶茴摇摇头。
“那我们聊聊天吧。”
“好。”于是,她身子一倒,背对着张庭园躺下。他们没有任何接触。
一整晚他们都没有任何接触。
那一晚,张庭园说了很多很多。从父母离异到家里空无一人,再从断臂之前和前女友的深厚情谊,再到断臂之后的人鬼殊途:十六岁那年,张庭园坐着摩托车载着交往两年的女友在马来西亚的新山驰骋着。那时,他的网站刚刚收到投资,几个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庆祝一番。
事故的发生并不戏剧性,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只是张庭园的一个走神导致车身失控、撞上防护栏,然后摩托车漂亮地弹起、旋转,把张庭园甩在栏杆上,把女孩甩下山谷。
张庭园说:“那天,我用尽全力,就想再看看她的眼睛,可是,天太黑,她戴着头盔,我什么都没看见,她就消失了。事故瞬间,她还在睡觉,估计摔下去时也没醒来,因为我一声尖叫都没听到。我多希望她是睡着死去的。”
“这是我的过错。她父母对我很好,竟然没有起诉我。已经两年过去了,很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时光可真是残忍。”
李叶茴静静听着。张庭园从仰躺着转向她,墙上两个人重叠的阴影也变高了,然后床铺上的世界又安静了。
“为什么不去米国读书?”李叶茴轻轻问出内心深处的疑惑。
“其实不是高中,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消失了。奶奶说他们去了米国,要我在新加坡乖乖地等他们回来。他们从来没回来探望过我、也没有电话打来。我怕我去了,机场却没人接我,只要我在这里等,我就还有爸爸妈妈。” ,空气凝固了,他接着说:“你是个神奇的女孩,让人有倾诉的冲动。我从没和别人讲过这些事情,甚至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没有。”
李叶茴问:“你现在开心吗?”问完她就后悔了。
“不。”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也不开心。”李叶茴讲。
张庭园的故事让她内心柔软而放松,但她不敢转身,怕本美好安静的夜晚又被沸腾的青春躁动抢了风头。
“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作为交换,李叶茴想说说自己的秘密。
漆黑的夜又从没拉紧的窗帘缝灌入这个房间,将这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深深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