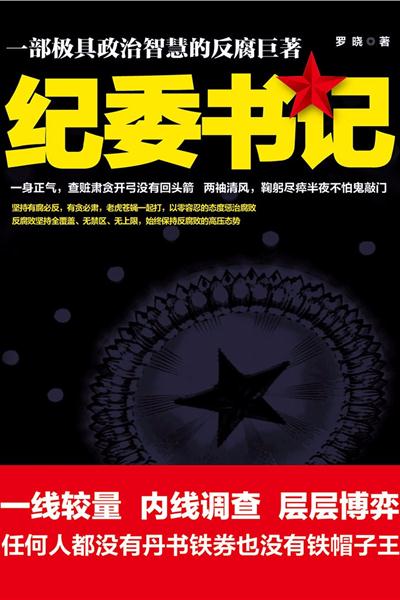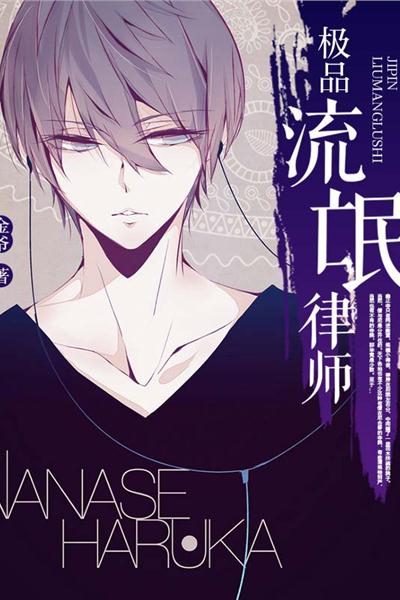对面的温惠,一身白色的休闲装,头发作了拉直,我忙碌了一天,此刻静静的坐着,享受着这份美女带来的清爽。
今天我们吃饭的饭馆紧靠海边,傍晚时分,沿海岸布置的夜灯亮了起来,如夜空中的繁星,蔚为壮观。
“怎么了,坐了半天都不说话?”温惠举起高脚杯,血红的葡萄酒在里面晃动,关心的问我。
我也举起酒杯,跟温惠碰了一下杯:“美女当前,秀色可餐,一时忘了说话。”
“没个正经,我看你面色有些发黑,最近火气比较大吧?”温惠问,目光仍然注视着我的神色。
“没事啦,公司新在角塘设立了一个商场,杂务比较多。”我打起精神,笑着说。男人嘛,不想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在女人面前。
“你要好好调理调理,火气大对身体不好,要煲些去火气的汤来喝。”温惠说。
我最近忙破了头,连阿莱都没时间去见,已经快一个月没有接触女人了,心说你就是最好的去火良药。但温惠这样的女人带到床上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好比一个饥饿的人望着满桌子的大餐,却不能吃到嘴里,难免觉得有些郁闷。
于是端起酒杯,跟温惠碰了一下,一口喝干:“唉,没办法,事情太多。有时我真想跳出这个圈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游。”
温惠从上学到工作从未出过远门,对旅游竟有点神往,也将杯子里的酒一口喝掉:“我还从来没有离开海门,外面的世界很美吧?”
我伸过手去在她的手上拍了拍,暧昧的说:“我带你去,让我们漫无目的的旅游,然后找个世外桃源,终老一生。”
“你不会把我给拐卖了吧?”温惠调皮的说。她调皮的时候嘴角上翘,两个酒窝若隐若现,令我心里一动。
“不会,不会,你也没多少斤两,卖不多少钱的。”我给温惠的杯子斟上酒,笑着说。
窗外海水泛着银光,映照着岸上林立的高楼大厦,夜色如此美好。
“你相信有真的爱情吗?”温惠转了话题,问了一个规矩女人都想弄明白的问题。
“你想听什么样的答案?浪漫的?还是现实的?”
“浪漫的怎么说?现实的怎么说?”
“浪漫的说爱情当然是有的。《西厢记》里张生初见崔莺莺,莺莺走后,张生有一句唱词: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说的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的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经典的爱情故事。”
“那现实的说法那?”
“现实的说,爱情也是有的。”
“哦?”温惠有点惊讶,她以为我会说没有。
“据科学家研究,男女相悦,大脑里会分泌一种物质,使大脑兴奋,这也是我们见到喜欢的人特别高兴的缘故。”
“想不到你这个人邪邪的,还知道这么多。”
“那你大脑是不是已经分泌了什么物质?”我邪邪的一笑,端起了酒杯跟温惠碰了一下,“来,促进一下。”
“酒能促进爱情吗?”
“酒可能促进不了爱情,却能促进性。”
“去,这点酒就想灌醉我?”
温惠说得不错,海门的女孩子真的很会喝酒。海门本地人历来有酿米酒的习惯,海门女孩自小在米酒的熏陶下,酒量还都可以。曾经有几次我不知根底,被海门女孩灌醉了,出了很大的洋相。
“那你是不是想让我灌醉呀?灌不醉你就装醉如何?”嘴里这么说,酒却不再劝她喝了,我还不想露出登徒子的嘴脸。
温惠有些羞意,低头吃着清蒸桂花鱼,一时无话。
男女的交往其实就像一场战争,双方都在试探性的伸出触角,意图征服、占有,在对方的领土插上自己的旗帜。人们给这场战争一个好听的名字:爱情。那么试探的过程当然就是谈恋爱了。
生活说到底是很简单的,只是人们刻意的把它搞得复杂。
漫步在酒店外的沙滩上,夜已经有点深了,晚风中带来了海水些微的腥气,一对对恋人各自寻找自己的角落,依偎在一起。在一个小沙丘,温惠和我坐了下来,沙滩被炙热的太阳晒了一天,此时还可以感受到微微的暖意。温惠虽然坐在我身边,却矜持的保持着距离。风带起了酒意,我不由感到一阵烦燥,铺垫了这么久,不知道究竟还要不要继续玩这种温文尔雅的恋爱游戏。大脑里一时竟不知如何进行下去,便倒在沙滩上,仰望星空,感受沙子带来的舒适的暖意。
夜空只有一轮残月,竟没有一颗星星,我越发失去了寻找话题的兴趣,听着海浪拍打着沙滩,心想等着温惠说点什么吧。兵法有云:敌不动我不动。温惠却静静的坐在那,沉默犹如夜色般蔓延在我们之间。
不知过了多久,见我有段时间不说话了,温惠转过头来,问我:“你是不是很累?”
我对这个过于矜持的女人有些恼火,感觉必须做点什么,即使粗暴的做点什么,便伸手一拉她的胳膊,她的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倒在我的怀里,我的嘴唇就吻上了她的脸颊。
温惠挣扎着想要起来,我紧紧的搂住她,不让她有逃脱的余地,嘴唇已寻找到她的嘴唇,就不管不顾的吻了下去。她的嘴唇很软,吸到嘴里给人一种柔柔的感觉。
温惠不甘就范,身体僵硬,头往后仰,还在胡乱的挣扎着,这越发刺激的我脑袋发热,舌头便用了力,顽强的撬开她的牙齿,与她的舌头纠缠在一起。
温惠的身体软了下来,放弃了抵抗,听凭我肆意的将她的舌头吸进嘴里,一股令人陶醉的纯纯的女人味道,不夹杂任何男人的气息,犹如家乡五月初熟的草莓,甜甜的,带点酸意。
忽然感觉脸上湿湿的,细看温惠已是梨花带雨,我不由得意兴阑珊,泛滥起的热潮瞬间退去,便松开了胳膊,任由温惠坐了起来。自己仍然躺在沙滩上,脑海里一片空白,懒懒的等着温惠发作。
这已经是第二个将眼泪流到我脸上的女人,她是否会像李延一样离我远去哪?
“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冲动,对不起。”虽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男人嘛,还是要绅士一点,看温惠并没有发作什么,我主动道歉。
温惠坐在那,好长时间什么也没说,却已经停止了流泪,沉默让空气都尴尬起来。
我站了起来,说了一个陈旧的笑话:“好了,你不会以为接吻就会怀孕吧?如果你怀了孕,我会负责的。”
温惠还是不说话,神情却有些缓和。
“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我见僵局无法打破,只好放弃,心里打定主意,再也不约这难搞的女人了。
一路上,温惠只是静静的坐着,面无表情。
肖邦的夜曲轻柔的漂浮在车厢内。
我很喜欢肖邦,他有时魔鬼般神秘莫测,有时又有如水妖般令人销魂,夜曲更是他孤独中的梦幻,在向深夜诉说着内心的渴望。此时的我沉浸在夜曲的氛围中,感觉温惠就像深夜的幻梦,虽然舍不得放弃,却还是要在黎明时离去。
车到了温惠家,温惠打开车门就要下车,我心里有些不舍,拉住了她的胳膊,说:“对不起,”温惠用力要挣脱,我急忙放手,嘴边的话再也说不出了。
我坐在车里,看着温惠头也不回的走进家门,心里怅然若失,这个女人可能再不理我了。
有些酸葡萄心理的男人常常会说:女人关了灯都是一样的。怎么会一样哪?花有百种,牡丹与兰花会一样吗?环肥燕瘦,女人各有各自的风情。我现在已经后悔自己的急躁,惊飞了这只清纯的白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