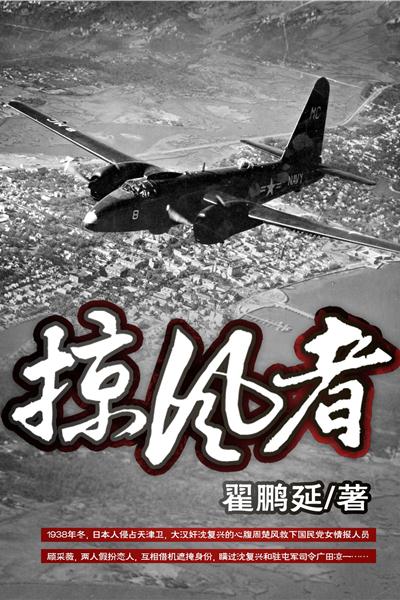“小弟听说大哥晋升了指挥使,高兴得一个晚上都没合眼,大哥一召唤,小弟立马赶来,一路上在驿站换了三次快马,日夜没停地赶着。”诸世明道。在这帮弟兄里,他的地位仅次于田尔耕。
田尔耕双手抓着他的两肩,摇晃着道:“嘿!几个晚上没睡,精神还这么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诸世明又对众人道:“大哥荣升为指挥使,咱们应该对大哥行跪拜大礼!以示祝贺!”
众人一听,全都扑跪下来:“恭喜大哥荣升指挥使!”
田尔耕笑着道:“起来,起来,都起来坐,咱们是哥儿们,不讲这一套。”众人起身后,依次在田尔耕的两旁坐下。
田尔耕跟着落座:“今天我把大家请到天津卫,是有些话在北京说不方便。因为锦衣卫里还有骆思恭留下的亲信。这不方便的话,就是攘外必须安内,眼下不少只会空谈、没事找事的东林党,一直在和魏公公捣乱。”
过开生愤愤地道:“魏公公是皇上最信得过的忠臣,谁反对魏公公,谁就是反对皇上的逆贼!”
“小过子说得对,不管谁反对魏公公,我们都要用些手段,巧妙地教训他们!注意,我这个‘巧妙’,大家一定要好好领会。”田尔耕特别提醒道。
众人齐声道:“是!”
田尔耕扫了众人一眼,继续道:“我这样说,不是说满鞑子派来的奸细就不查了,但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要转移,首先要对付那些和魏公公作对的东林党!眼下边关吃紧,如果不把内部安定下来,怎么去对付满鞑子!”
“是啊!这帮吃饱了撑的文人,总是没事找事,不给他们点厉害看,咱们就不能集中精力对付满鞑子!”诸世明接着道。
田尔耕道:“阿明说得好!魏公公也是这么说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讲空话,这次我把大家找来,一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了。二是这些年来,骆思恭把锦衣卫搞得像和尚庙似的,我想让大家轻松轻松。大家得感谢这次聚会的主办人、天津卫的千户郑清明。好了,我的话完了,等会儿郑千户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坐在末位的郑清明一听,站了起来:“诸位请跟我来。”
众人跟着郑清明来到一间大厅的门口,厅里的宫灯把门口照得通亮,厅门是落地的双合拉门。郑清明在门口停下后,拍拍双手。庭内顿时响起《春江花月夜》的乐声,双合门徐徐拉开——厅里摆着美酒佳肴的大圆桌前,坐着的全是袒胸露臂、年轻貌美的姑娘,人数和锦衣卫的头儿们相当,场面极其香艳。她们一起微笑着朝门口锦衣卫的头儿们招手。
这些哥儿们个个露出亢奋的惊喜……
连日来,李永芳表面平静,心头却盼着北京的天亮能把情报送到。天亮主要是用信鸽递送,虽说信鸽比人送得快,然而安全系数不比人高,尽管天亮带去的信鸽都是名种,而且经过武长春精心调训,野外的生存能力很强,但是北京离东京(辽阳)的空中距离是两千多里,途中气候多变,天敌甚多,遇到意外的概率不小。他相信此时天亮已经放飞带着情报的信鸽,关键是这只信鸽是否能躲过天敌,顺利抵达。这几天一股寒流正在南下,他为那送情报的鸽子担心呢。他正坐在签押房内想着时,武长春推门而进,高兴地说:“阿爸,天亮报丧的帖子到了,舒哈达在北京建的那条细作网全军覆没,无一幸免。”
李永芳一听,刷地站起:“还有什么消息?”
“锦衣卫的头儿骆思恭被升任为太子太傅,而佥事田尔耕被任命为锦衣卫的指挥使!”
李永芳冷冷一笑。
“阿爸可是觉得骆思恭是明升暗降,被魏忠贤踢到了楼上?”
“正是,田尔耕很可能是被魏忠贤收买了,他上台后,肯定会把精力放在对付东林党人的身上,这对我们重新布置线人、安插卧底、收集情报倒是极为有利。”李永芳说得十分肯定,颇为自信。
“阿爸说得是。”
李永芳看着武长春,又道:“你马上写份报告,我亲自去送给舒哈达。”
“阿爸为何不直接交给四贝勒?”武长春对李永芳的吩咐有些意外。
“这一个消息对咱们的主子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如果我直接去向四贝勒报告,弄不好他会怀疑我幸灾乐祸,有抢班夺权的野心,而我向舒哈达报告,他再转报给四贝勒时,这小子肯定会推卸责任,说我坏话,我就是等着这小子的烂舌头说我坏话。”
“阿爸认定四贝勒听不进舒哈达说您的坏话?”
“不错,要是这小子委过于我,说我坏话,以我对四贝勒的长期观察,凭着他的精明,他会觉得这小子心胸狭窄,妒才嫉能,不宜在这个位子上待下去,至少会把他架空。”
武长春一听,佩服地:“阿爸高见,我敢保证,舒哈达这小子肯定会在四贝勒面前说阿爸的坏话。阿爸,您出头之日到了,到时候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但愿如此吧!”李永芳又看了一眼兴奋的武长春,长叹一声道:“长春,其实朱明皇朝对我不错,把我从一行伍提升到独当一面的抚顺游击。当年大汗兵临抚顺城下,我也曾想听从你的意见,坚守抚顺,后来我反复思考,朝廷里阉竖当权、奸臣当道,东林党人只会空谈瞎闹,他们明争暗斗,全然不顾国家的安危,那些为国着想的能人,如熊廷弼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让人心寒,我不向满鞑子投诚,迟早是死路一条,现在你总该看清了吧!”
“看清了,孩儿现在才深深感到阿爸的高瞻远瞩,不然,咱们早就成为黄土一堆,死无葬身之地。”
“你能这样想就好,我们这样做也是顺从天意。”说到这里,李永芳的口气里充满无奈。
李永芳带着武长春写好的报告,来到舒哈达的都护府时,得知舒哈达不在,刚去阿巴泰家,于是便对舒哈达的书记官道,他有重要情报向指挥使报告。都护府有规定,有重要情报随到随报,书记官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去阿巴泰家通知舒哈达。书记官估计舒哈达会在阿巴泰家打马吊牌,这是明代王世贞发明的一种游戏,它的玩法近于后世的麻将,是从关内传到关外,如今在八旗贵族家十分流行,阿巴泰的牌瘾极大,他今天去阿巴泰家是带着一副极为珍贵的翡翠马吊牌的。
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个儿子,颇有勇力,但他头脑简单,性格倔强,脾气暴躁,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独他敢顶撞这位大汗,所以他也是努尔哈赤最不喜欢的儿子,至今没被册封贝勒。他一见到舒哈达,便高兴地问:“阿达,您可是个大忙人,好久没来我这儿了,今天怎么有空来?”
“奴才来给七阿哥转送件东西。”舒哈达与阿巴泰关系极好,情同兄弟,但阿巴泰是大汗的儿子,按照礼数,关系再好也须自称奴才。
舒哈达把一个锦缎盒子递给阿巴泰。他打开一看,是一副翡翠马吊。他又摸出几个马吊牌,欢喜地看着。
舒哈达见他欢喜,便道:“这可是用上好的翡翠制的,我敢保证在东京城里没有第二副。”
“是不是齐格勒让你送来的?”阿巴泰马上猜到,他知道舒哈达并不热衷打牌,只是因为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偶尔陪他玩玩,不会花心思去搜罗这样珍贵的马吊牌。
“正是,不瞒七阿哥说,奴才是受齐格勒委托来提亲的,他很想当七阿哥的乘龙快婿。”
“那我就把三闺女赫梅芳许配给他。”
“可他看中的是二格格赫梅蓝。”
阿巴泰苦苦一笑:“这事他早就派人来试探过,我问过赫梅蓝,她不愿意。”
“你是赫梅蓝她爹,这事该由你说了算,齐格勒他爹曾是大汗的左膀右臂,战功显赫,如今齐格勒弓马娴熟,勇武过人,很受大汗赏识,这么年轻,就让他袭了他爹的镶红旗的副统领,真可谓是前途无量。奴才以为,也只有他才配得上聪慧漂亮的二格格。”
“不瞒你说,我是看着齐格勒长大的,知根知底,一直挺喜欢他的,我也不瞒你说,几个孩子中,我最宠爱的就是赫梅蓝,你别看这孩子表面上挺和气的,可是主张可大了,她不愿意的事,你说啥都没用,我也拿她没法子。”阿巴泰叹着气道。
阿巴泰的出名,除了敢顶撞身为大汗的父亲,再就是他的娇惯子女。他的长女嫁给了蒙古王公的儿子,因为受了丈夫的委屈,回家告状,他便叫两个儿子去把他女婿打得半死,足足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此事在东京(辽阳)轰动满城,努尔哈赤极为重视与蒙古的联盟关系,为此,还当着蒙古王公的面扇了他两个耳光。阿巴泰算是唯一挨过大汗耳光的儿子。
“齐格勒不是和二格格一起长大,她从小就叫齐格勒为齐哥吗?”
“正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她说只能把齐格勒当哥哥,不愿当他的老婆。”
“那你找机会再和她谈谈,齐格勒说,非赫梅蓝不娶,他等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岁,还没有娶亲,为的就是要娶赫梅蓝为妻,这样痴情的好小伙子,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阿巴泰想了想,又看看桌上放着的翡翠马吊,才道:“那我就找机会再与她说说,但你要告诉齐格勒,这事不能太急。”
舒哈达高兴地说:“奴才一定转告。”
就在这时,舒哈达的卫士进来说:“指挥使,刚才李永芳说有重要情报向指挥使报告,他在都护府里等着主子。”
舒哈达一听,便向阿巴泰告辞离去。
皇太极正与二福晋博尔济吉特在书房内下着围棋。
三十出头的皇太极面色红润,相貌俊朗,体格强壮,举止稳健,那种非凡的气质绝非常人所有。他那蒙古裔的福晋更是个绝代佳人,美丽的脸上透着那种女性的精明。执黑的博尔济吉特把一个棋子落下,皇太极十分惊异地赞叹道:“福晋学会围棋还不到两年就能出此奇招,吃了我这么一大块地盘,我认输了。”
博尔济吉特笑道:“谁都能认输,就是贝勒爷不能认输。”
皇太极也笑道:“除了您,我在谁的面前也不会认输。”
此时一卫士进来报告:“贝勒爷,舒哈达有紧急情报禀报!”
“让他进来吧!”
卫士退出片刻,一脸沮丧的舒哈达走了进来,扑通跪下:“贝勒爷,奴才该死……”
皇太极一惊:“出了什么事?”
“我们多年经营,在北京和山海关的细作网被南朝的锦衣卫破了。”
“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皇太极的眉头顿时紧锁起来。
“先是李永芳从他私下安排的细作那儿得到消息,向奴才作了通报,奴才正想派人查证时,有个侥幸从山海关逃脱的细作前来报告,证实了李永芳的消息没错。”
皇太极愣了好一会后,生气地说:“李永芳不是早就提醒你,锦衣卫已经盯上了我们的细作,我也要你采取措施吗?”
“奴才已经派人去提醒了,从时间上推算,奴才派去的人还没有到,锦衣卫已经动手了。”
皇太极思索时,博尔济吉特提醒道:“贝勒爷,让舒哈达起来吧!”
“你起来吧!”
舒哈达起身后,看着思索着的皇太极,问:“四贝勒,有一些话奴才不知该不该说。”
皇太极冷冷地:“说吧!”
“奴才记得,李永芳曾对四贝勒说过,咱们一定要提防内鬼,奴才觉得,我们在关内的细作网被锦衣卫破了,肯定是内鬼捅出去的。而奴才认为,这最大的内鬼也许正是说有内鬼的李永芳。”
皇太极一听,直视着他:“你凭什么这样说?”
“奴才总觉得李永芳是个汉人,与咱们满人不是一条心,他背着我另外往北京派人。”
“是我叫他派的,情报的来源不能是一条线。”
舒哈达大感意外地怔了半晌才道:“他派出的人不一定可靠,没准,就是其中有人把我们的细作网捅给了锦衣卫,奴才觉得,汉人缺少忠诚,绝不能重用。”
皇太极听了这番话没有回应,而是反感地问:“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没了。”舒哈达感觉出这种反感,泄气地道。
“那你就回去吧!”
舒哈达离开后,皇太极依然在那儿苦思冥想。
博尔济吉特起身,给皇太极面前的茶杯添满茶水后,道:“贝勒爷,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场上是这样,暗中谍战也当如此。咱们关内的细作网被破了,可以再建再派,没啥大不了的。”
皇太极看着这位福晋,拧着的眉头松弛下来。这时,努尔哈赤的贴身护卫库哈图走了进来。皇太极一见,站了起来:“库哈图……”
库哈图施礼:“贝勒爷,奴才奉大汗之命,前来传召贝勒爷随大汗行猎,时间可能要两三天,贝勒爷得多做些准备。”
皇太极略一思索,又问“这次皇上都传召了谁?”
“就四贝勒一个。”
皇太极并没有显出高兴,而是平静地道:“你先回去,我准备好后,马上去大汗那儿报到。”
库哈图转身离去后,博尔济吉特看着皇太极:“贝勒爷,大汗今天的心情挺好的,他好久没去行猎了,而且又单独叫你随行,你该理解其中的含义,可别一见到他就把细作网被破的事告诉他,坏了他的好心情。”
“福晋说得是。”
昨晚努尔哈赤睡得特好,起床后拿起一本刚从关内弄来的新黄历,翻到当天的一页,上面写着“宜狩猎”。对于黄历上说的,他的态度是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他放下黄历,伸展了一下结实的双臂,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朝窗外看去,只见透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对面宫室那金黄色的琉璃瓦在艳阳的照耀下熠熠闪光。庭院几株秋海棠非但没谢,而且开得十分繁盛。已经是九月十七了,往年的辽东都下霜了,如今却温暖如春,是个真正的小阳春,这样的天气确实是宜于狩猎。虽说这位后金大汗已六十开外,但他发誓灭明、入主中原的雄心更加坚定,另外,还有两件事情上他兴趣丝毫不减:一是女人,昨晚临睡前,被他宠幸的年轻爱妃阿巴亥就充分感受到他那非凡强健、常人少有的雄风,得到极大的满足;二是狩猎。他认为人越老,越要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打仗是动,没有仗打狩猎也是动。他们这些天池女神的后代,所以能体魄健壮,骁勇善战,完全是缘于狩猎为生,弓马娴熟。他还认为一旦入主中原,子孙们也不能丢弃狩猎。